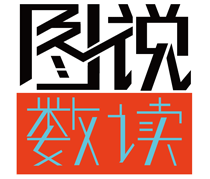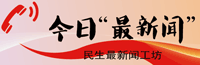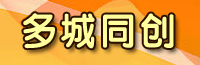橘花開了。
它是數(shù)著日子開的:清明含苞,谷雨綻放。修長如指甲的白色花瓣,一片、兩片……五片,五片花瓣圍著嫩黃的花蕊打開,細細小小,白瓷一般讓人不忍觸碰。
在花瓣綻放的剎那,橘香像個胖滾滾的小精靈,逮著機會滾落下來,撒著歡兒,四處奔跑。
橘香啊,它長了腳。在晨光初起的時候,它已經(jīng)從十幾里外的橘園,跑到了我的窗前。當我推開門窗的瞬間,它就撞了進來——花香幽幽的,有點兒甜;閉上眼,深深呼吸,嗯,五臟六腑都覺得舒坦。它越過我,在房間里開心地翻了個筋斗就跑了,只留絲絲縷縷的香氣若隱若現(xiàn)。
清晨的陽光,松松灑落,空氣清澈舒爽。千年石橋五洞橋橫跨西江兩岸,橋面一波五折,橋下是五個弧形的橋孔,橋孔與水中的倒影相連,宛若大大的“五環(huán)”立于江面。
它開心地在“環(huán)”上滑滑梯,慣性將它帶飛起來,沒等它站穩(wěn),又嚇得跌落河中,稚嫩的腳掌在水面慌亂撲騰,蹬出無數(shù)環(huán)形波紋,一層層圈開,香氣隨波蕩漾。
它沿著官河奔跑,記憶熟悉而又陌生。“九曲澄江如練,夾岸橘林似錦”“吾邑環(huán)西南城外皆桔柚之園,千株萬株,不勝屈指數(shù)”“路入綠蔭春未老,細花如雪惹衣裳”……
畫面變幻中,它終于記起——曾經(jīng)的曾經(jīng),河流縱橫的古城,兩岸遍植橘樹:東自江口,沿永寧江、西江、南官河及其他支流兩岸,都是屬于它們的橘園呀!每當清明、谷雨,滿城橘花次第開放,它們快樂地翻滾著,一路向東,向更加浩瀚,更加遼闊的東海奔去。
如今,官河穿城而過,把城市劃開兩個區(qū)域:半城是煙火,半城是詩意。官河兩岸行人悠閑地散著步,河水泛起波瀾;官河外車水馬龍,人聲嘈雜,匆匆忙忙的腳步為生活奔波。
橘香停下腳步,在人來人往的街頭,頑皮地用小手輕輕在你肩頭碰一下,悄悄跑開;又在他肩頭碰一下,再悄悄跑開。于是那香氣倏忽來,又倏忽走。忙碌的人們忍不住停下腳步:“好香呀!”“是什么這樣香?”“原來是橘花開了呀!”
橘花開了。十里開外的橘園霎時熱鬧起來,人們結伴而來,賞花、聞香、吃食餅。一只只嫻熟的手將米粉干、蛋皮、鹵肉、蝦仁、黃鱔、墨魚、土豆絲、豆腐干、茭白、豆角、蒜薹等等,包在食餅皮里面卷起來,而正在貪婪吸吮的橘香差點兒也被卷了進去,在人們張嘴的瞬間,快速掙脫。于是一閃而過的香氣劃過鼻尖,味蕾被花香喚醒,食餅吃出了與平日不同的味道。
橘花的溫情不會外泄,想體會它的美麗,你不能匆匆走過。
日頭攀上橘神雕像的瞬間,十萬朵花苞同時炸裂——小小的、白色的花,藏在綠葉中間,像一串串白色鈴鐺。鈴鐺越掛越多,最下面的白色花瓣承受不住,便簌簌落下。很快,橘樹下就鋪了一層雪。這香甜里藏著多少來不及,就像中年才懂的,所謂盛放,不過是一場緩慢的凋零。可是那又怎樣呢?生命從來都是向死而生。
那些新生的香氣赤裸雙足,踩著滾燙的泥土舞蹈。蜜蜂聞香而來,從四面八方而來,嗡嗡嚶嚶,嗡嗡嚶嚶,合著它的節(jié)拍,繞著淡黃花蕊跳起華爾茲:一二三,一二三……陽光這樣的美好,花朵這樣的鮮妍,小蜜蜂興高采烈。阡陌縱橫處,詩幔撩起長長水袖,踩著節(jié)拍滑入橘園舞池。它的身上是詩人寫給橘花的情書:
一朵橘花就是
一盞小小的酒盅
如果我稍微慢一點
就會從心里
長出拔節(jié)的陽光……
橘花羞澀地躲在葉子下面,不敢直視這樣的熾烈。
炊煙升起時,亭子里賣橘的村婦站起身,裝滿橘子的竹籃挎在手臂,沉重地壓彎了她的腰肢。跨季儲存的橘子早已不受歡迎,她嘆息一聲,蹣跚走回家中。橘香攀著她的衣褶,輕輕撫上她皺起的眉頭,似乎想提醒她:“再過幾個月,新的橘子就會掛滿枝頭……”村婦身旁的大黃狗不小心被橘香的腳趾勾住,猛地搖搖尾巴,往前跑遠了。
不遠處的岱石山上,石大人依然癡癡地眺望愛人。每當橘花盛開,他就會想起那么多的往事。
夜色隱藏了他的面容,橘園在月光下明亮起來——一朵朵盛開的橘花就像滿天的繁星,閃著溫潤的光芒;橘香慢下腳步,在夜風中蕩起透明的秋千。
其實月夜下的橘園更美。坐在橘園里的座椅式秋千上,蕩呀蕩,花香在鼻尖縈繞,悠遠綿長。抬頭看天,有幾顆疏朗的星星,只覺天遠地闊。“醉后不知天在水,滿船清夢壓星河”——呵呵,閉上眼睛,聞著花香,吹著晚風,我真覺得自己醉了。
有一種花……我想,它把一個城市馴服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