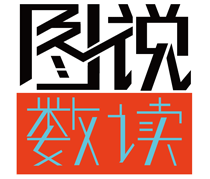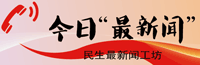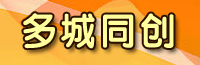它伴著柔和的風緩緩地從我眼前飄過,擾亂了我額前的發絲。我伸出手想抓住它,它卻敏捷地從我手中鉆過,只留下細微的觸感,似有似無。坐在窗前,攤開早已陳舊的書籍,視線卻突然在其中略鼓起的一頁上停留,上面靜靜地安置著一朵不知何時夾在里面的橘花,形態完整保留著,只不過花瓣因為缺失水分而變得干癟,伸手還能觸碰到它的紋路,我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揚,思緒也漸漸飄遠。
當初夏的風裹挾著濕潤的綠意輕輕掠過山崗時,我忽然被一縷清甜的香氣絆住了腳步。抬頭望去,幾樹橘花在綠葉間悄然綻放,像被晨露浸透的月光,碎銀般灑滿枝頭,這些橘花總讓我想起童年老家的庭院。故鄉作為蜜橘之鄉,每個庭院總少不了在自家院角種幾棵橘樹。每當橘花開時,枝頭便綴滿細碎的純白,星星點點,煞是好看。而淡淡的花香卻若隱若無,清新明快。我和小伙伴總愛在綠蔭底下追逐嬉鬧,又或是踮腳摘花,花瓣沾在發梢,連過堂的風都帶著一縷香氣。那時不懂賞花,只覺得好看,卻不知這香氣里藏著時光的暗語。午后蟬鳴漸起,橘花愈發顯得矜持。它們不似梔子花濃烈,也不學茉莉花扮甜膩,只是淡淡地懸在枝頭,任由陽光從花瓣的縫隙漏下,在地面織出一片流動的光斑。偶爾有蜜蜂闖入花叢,笨拙地跌進花蕊深處,驚起了整樹花朵顫動……
當然最壯觀的花海在橘林,每當晨霧散開,枝椏間垂落的蛛網上便綴滿細密水鉆。奶奶教我辨認五年生的橘樹:“開枝散葉像傘骨的才肯結甜果。”她的藍布衫掃過灌木叢,驚起幾只花蝴蝶。我們循著暗香往橘林深處走,忽然撞見整片低垂的花瀑——三十年樹齡的老橘樹正開得忘情,米白花朵攢成繡球,壓得枝條幾乎都觸到了新翻的土壤。“這才是真正的橘花。”奶奶踮腳采下一簇半開的花苞。露水從她發梢滑落,洇在土布衫上暈出深色的圓。花蒂折斷處滲出透明汁液,沾在指腹竟像摻了薄荷的蜂蜜,我總忍不住地把指頭伸進嘴里。
日頭攀上瓦檐時,祠堂前的石臼開始被曬得溫熱。奶奶支起杉木案板,老銀鐲子磕在陶盆上叮鈴作響。我們圍著青石臼搗花泥,木杵起落間,白花瓣漸漸融作玉色的漿。她一邊搗一邊念叨著老輩傳下的方子:“一斤花三兩糖,要曬足七個日頭哩。”我累了便趴在祠堂的條凳上打盹,朦朧間看見奶奶在曬匾前翻攪花糖,她說曬足日頭的橘花糖會凝出雪晶似的糖砂,正如村莊的往事會在歲月里析出沉香一般。暮色四合時,家家灶間騰起白汽。新蒸的橘餅碼在粗瓷碗里,琥珀色的糖霜裹著半透明的花瓣,個中滋味只有嘗過才能細細體會。晚風掠過橘林,卷著殘香漫過圍場,蕩過祠堂,最后纏繞在家家戶戶的前屋后院。而那些白天收攏的花瓣正在月光下靜靜呼吸,四野寂靜,唯有螢火蟲在默默地打著燈語。
夜深了,我望著山崗上的橘花在暮色中漸漸消隱。感嘆如今在城市高樓間難覓橘樹蹤跡,但每逢初夏,總會在某個轉角與橘花重逢。它們或許藏在公園角落,或許棲在陽臺花盆,以不變的姿態綻放。忽然明白,那些年追著花香奔跑的歲月,早已在心底開出了一樹橘花,年年歲歲,清香如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