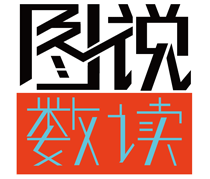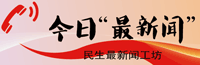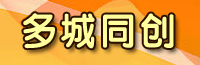我在柜櫥的角落里,找到那個蒙塵的黃色塑料盒子時,父親已經離世近五個月了。盒蓋掀開的瞬間,細微的塵埃在光線里浮游,像被驚擾的時光碎片——久違的鋼筆們,支支攜帶著歷史重量:英雄100號,永生212,那支產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藍灰色上海牌金筆,筆尖依舊金黃,筆桿處雖有一道淺淺的裂痕,但筆桿還溫潤如玉。盒子底部,竟然躺著幾個早已被我遺忘的銅筆帽,泛著暗黃色質感的啞光,年幼時,它們曾是我洗凈的毛筆上身份高貴的“頂戴”。幾十年間,經歷數次搬家,由北而南,由鄉而城,父親竟然完好地保存著這些跟隨他走南闖北的筆們,視若拱璧。
父親的字好,有扎實的書法功底,軟筆硬筆俱佳,如行云流水,又似古松盤虬。他在學生時代,曾經幫老師刻鋼板,出試卷,工整嚴謹,力透紙背。漢字和阿拉伯數字都毫不遜色,宛若機器刻寫。刻板的規范書寫,并未減損父親書寫的另一面:恣意灑脫。他的行草線條流暢,含蓄與寫意并存,筆走龍蛇間,氣息、力量,對象形字的理解都在其中。他的手渾厚有力,我曾見他蓄力腕間,行云流水地潑墨。那氣度,仿佛王者,縱橫捭闔,瀟灑人間。
在我初中畢業的那年暑假,父親看看我的字,搖搖頭說,你這寫得都是有棱有角的方塊字,難看。我教你學草書吧,上高中要快速記筆記。他教我寫的第一個字,就是草。“草圣最為難,龍蛇竟筆端”。這是我學習草書最先接觸到的一句話。草和學,在草書中很容易混淆。父親一再教我辨別。此后,他專門找差不多的字一塊兒講解,加深我的記憶。他經常握著我的手,跟著他的手起勢、舒展、折返、點頓,仿佛牽引著幼童習步。我逐漸能體會筆意間的流動自由、節奏快慢、筆勢收放——時而如淺溪里游魚迂回,時而如舞臺上水袖輕舞。他演示“飛”的四五種寫法,果然每種都藏著不同的風姿,種種飄逸如蝶。由此,我漸漸找到書寫之樂,筆下的字漸漸不那么正方,線條逐漸流暢灑脫起來。當我把幾個常用字寫得有模有樣時,父親不免開懷,用他特有的拉長音調的“哦”字,夸張地表示驚訝:這是你寫的還是我寫的?都可亂真了。我深知,這是他以特殊方式對我的的鼓勵。
“字是頭碗菜。”父親總說這句家鄉俗語,他說字如人的臉面,字好,為形象加分。他總是督促我把字寫好,一方面教我草書,另一方面也督促我寫正楷,可惜我沒有堅持下來。我缺乏毛筆功底,學父親的字,也不過得了三分精髓。像一個學了幾天武功的人,不過花拳繡腿架子好看,缺了骨感,甚為遺憾。
前幾天,在書櫥里發現一本線裝的舊字帖,里面夾著一沓子400格的綠框手寫稿,泛黃的紙頁間飄出陳年松煙的氣息,不知道是他何時所寫,內容是舊字帖目錄索引。我驚訝地看著他一筆一劃的鋼筆字,精致靈秀,暗藏功力,筆筆帶著對文字的敬意。一張張地翻看這些舊紙張,幾乎聽到父親對我說,你看,你寫的橫折鉤缺乏弧度,老是那么一挑就過去了,寫字要寫到位,要端得正。原來,父親留在舊紙頁間,浸透了歲月的深藍色墨跡,不過是要在某一刻讓我領悟——在生命的皺褶里,寫出光的形狀。
父親年紀漸長,手抖,很久不寫字。即便寫幾個字,線條也如洗舊的衣服,不再平滑流暢。疫情后,他進入護理院調養。身體稍稍恢復了一些,竟然萌生了出人意料的想法:年逾九旬的他要教老人們學書法。我和醫護人員一樣,認為他老糊涂了,在那個特殊地方,面對一群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,講書法,是多么不合情理,便想方設法地勸阻。有一天,他望著窗外遠處疾馳而過的動車,沉思良久后對我說起生命的空茫,是那種深深的無依,我才漸漸理解了他。他是在尋求生命的平衡感和寄托,看似荒唐的想法,不過是需要一種精神慰藉,來抵抗年老病痛帶來的虛空感。
去年暮春時節,父親病危進入重癥監護室,身上插滿了管子,無法發音。我每日下午陪伴他,看著他一天比一天衰弱而無能為力。一天下午,他情緒激動,嘴巴不停地說著什么,還夾雜著手勢。我扶他坐起來,叫護士拿來紙和筆,讓他寫下想說的話。他拿筆的手,已骨瘦如柴,皮膚和骨頭中間,是繡線般纖細的幾根小血管。但凡護工幫他翻身時手重了點,皮下血管就會破裂,在手背上洇出地圖狀的紫紅色斑塊,一如無奈凋落的花簇。這只手無力地握著筆,良久,終于在白紙上書寫起來,那是一堆纏繞在一起的線條,狀若古老的符咒,我仔細辨認才發現,他寫下的竟然是他和母親的名字,原來七十載伉儷情,早已融入骨血中。我用手機拍下他今生最后一次、也是最柔情的一次書寫,珍藏起來。他虛弱不堪仍不失風度的運筆氣勢,得到護士的夸獎:你的字一定很好,從握筆的姿勢就能看出來。他竟謙遜地,略帶羞澀地擺擺手。
父親隱遁于塵世,是在秋末的微涼天氣里。此后,是蔓延整整一個冬季的嚴寒。我借以取暖的一種方式,竟是無意識地重拾抄書之樂。每天下午,坐在書房里凈手書寫,既為靜心,又可練字。幾個月間,抄滿了兩個筆記本。這中間,有意識地把筆畫寫到位,寫工整。電子時代久不動筆,對書寫缺失了感覺,總覺得中性筆雖方便,但少了點什么,于是去父親房間尋覓,直到那幾支舊鋼筆神諭般地出現。
英雄,上海,永生,這些跟隨父親一生的舊鋼筆,現在被我重新收納,裝進一個新的盒子里,重新清洗并灌滿了新買的墨水。這天,我挑了一支他曾經握著我手寫字的黑色永生212鋼筆,用不太熟悉的方式重新握筆,筆尖劃過紙頁,有粗重的阻力,筆畫卻依然清晰。我努力把橫折鉤寫得圓潤到位,仿佛父親正站在我身后目視指點。寫著寫著,我不覺淚流滿面:爸爸,我想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