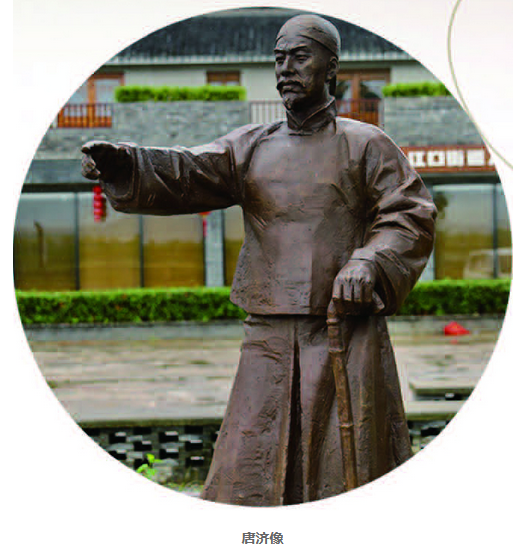
在黃巖永寧江下游三江口南岸,矗立著一尊青銅人物雕像,他身穿長袍馬褂,面對遼闊的永寧江,極目遠眺,躊躇滿志,但又若有所思,似乎正在籌劃著什么?他就是晚清太平(今溫嶺市)知縣唐濟。
一個地方官能被一方百姓所銘記,并以立像紀念,那他一定是做了造福一方的好事,而且福澤后世,影響深遠。說也奇怪,唐濟雖曾擔任黃巖縣知縣,但他卻以太平縣知縣的身份被江口人民銘記的。原來,江口地處永寧江、靈江、椒江三江交匯處,自古是水道要津,北通靈江,東達海門,南連東官河、南官河接溫嶺,自溫州、溫嶺南來的商賈、學子北去臺州府、省城,多數擇水路乘舟到此,再轉乘船經靈江,隨潮水而上到達臺州府城。反之亦然。那時,這一帶十分荒涼,沒有廛市,僅有數間供漁民居住的茅蓬。而旅客往來,沒有休憩之所,如遇暴風驟雨,衣履盡濕,狼狽不堪。清同治十三年(1874年)秋,唐濟赴任途中目睹此情此景,便籌款倡建郵亭曰太平亭,于亭北建廟叫天后宮,亭南為驛館,至光緒三年(1877年)春落成,至此往來稱便。此地因此日漸繁華,商旅往來,遂成街市,這便是江口街的由來。
因為唐濟而有太平亭,因有太平亭而有江口街,飲水思源,緣木思本,江口人民自然不會忘了這位造福一方的地方官。
唐濟,字星舫,廣西桂林人。監生,同治十三年九月初九日因軍功署太平縣知縣。除此,還曾擔任仙居、黃巖、遂安等縣知縣。《太平縣志》載:唐濟“初政卓異。其籌建太平亭、橫湖亭于黃邑三港口,以便赴試者憩息,洵善舉也。”
關于唐濟籌建太平亭的事跡,蔣驤云在《太邑公建黃屬三江口天后宮路亭碑記》有詳細記載:“三港口,在郡治東南。上接靈江,下通海門。凡天臺、樂安(今仙居縣)、蒼溪(今黃巖區)諸山從此入海。吾邑(太平縣)人由內河買舟達此,再乘江船晉郡,隨潮上下,風濤不測,時有顛危之慮。而地處要沖,內無廛市,沿堤茅屋數椽,臨流待濟,風雨驟來,衣履沾濡,蔭庇無所。同治甲戌(1874年)九秋,桂林唐星舫明府,奉檄權吾邑,篆道經此,目擊顛連,思所泰之,議于江岸創建神宇、郵亭,借托帡幪而資棲息。首捐廉俸百金,命邑紳襄其事。集資購址,鳩工庀材,經始于光緒丙子(1876年)秋,至于丁丑(1877)春落成。正殿五楹,供奉天后之神,左右廂各三楹。門外郵亭五楹,額曰‘太平亭’。其內河舍舟登岸處,亦建郵亭三楹,額曰:‘橫湖亭’,并便行旅暫憩,計費三千余金。皆由吾邑官紳商民資助,成此巨功,洵善舉也。”
與籌建江口太平亭相類似的,唐濟還在石塘與松門之間修筑避潮臺,這件事還曾引起上海《申報》的關注,在1875年11月6日的報紙上詳細報道了此事,題目是《唐明府筑臺拯溺》。《申報》在報道唐濟修筑避潮臺之余,還對唐濟的政績加以介紹,如“修城郭,設營房,浚水閘,益民之事甚多”“緝訪花會,安謐地方,嚴禁小錢,遵用官板,凡歷年流弊盡捐除”等。并以“美哉政乎!牧民者可以興矣”這樣的語句給予高度評價。
確實,唐濟在太平縣知縣任上,做了許多有利民生、功垂一方的實事。查考文獻,可知唐知縣還重建袁公祠,并在校士館內望鶴樓后修建藜照樓等。為此,唐濟撰并書有《重建袁公祠記》。唐知縣將祠內臨近街市房屋租給民戶,又將所收租費充作公用,且將各項收支勒于石上,條目內容細致合理,公開公正,既解決了各項事業的經費開支,減輕了人民的負擔,又免除了當時及將來可能產生的諸多糾紛,使之能夠長久維持。
上述事例表明:唐知縣在任內體察民情,心懷百姓,重視為民辦實事。除上文《申報》的高度認可外,《太平縣志》也給予其“初政卓異”的評價。
此后,唐濟于光緒五年(1878年)閏三月調任黃巖縣知縣,第二年三月離任。接下來數年,尚無文獻查考,不知調往何處。
光緒九年(1883年),唐濟任遂安知縣。遂安縣,浙江舊縣名,位于今淳安縣千島湖景區,縣境大部分湮沒于湖底。在遂安任上,唐濟修學校,葺城墻,建祠宇,勤政為民,政績可觀。4年屆滿后,在百姓要求下又留任。在這一任上,主持纂修光緒《遂安縣志》。
光緒十八年(1888年),唐濟回任黃巖縣知縣,二十年八月離任。在黃巖任上,唐濟未曾留下可供稱頌的政績,反而在光緒二十三年的《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》上還載有“黃巖縣知縣唐濟,辦事粗率,不洽輿情,著開缺另補”的條目,著實讓人疑惑。
總而言之,從唐濟在太平縣、遂安縣知縣任上的所作所為看,其仍不失為一位“為官一任,造福一方”的好官,值得后世銘記與頌揚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