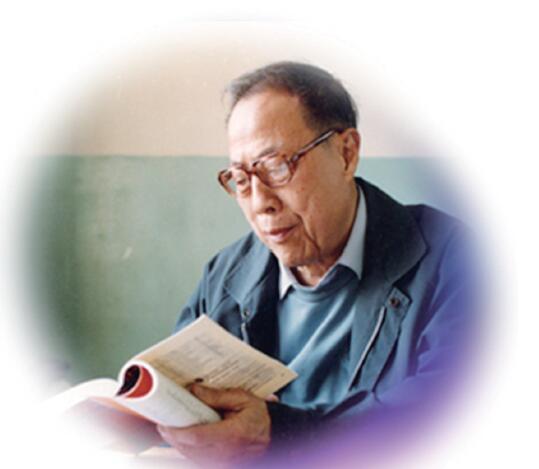
“我相信,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,無論是國防事業,還是民用設施,如果再有與‘兩彈一星’類似的大項目,只要在黨的領導下,發揮大力協同精神,我們一定能超越他人,圓滿完成。”——陳芳允
“人生路必曲,仍須立我志。竭誠為國興,努力不為私。”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里,臺州亂彈的演員們真情演繹著由陳芳允事跡改編的現代戲曲《追星者》,一首言志詩的深情朗誦,讓觀眾席里一位老者的眼眶泛了紅。
老人叫陳曉南,原國防科工委、總裝備部高級工程師,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。他的另一個身份是“追星者”陳芳允的兒子,“為國不為私,這首詩就是我父親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寫照。”陳曉南說。
陳芳允(1916.4.3—2000.4.29),“兩彈一星”功勛獎章獲得者、無線電電子學與空間系統工程專家,中國科學院院士,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理論奠基者及國家“863”計劃發起人之一。他少年離家求學清華,學成后將一生奉獻給了我國的“兩彈一星”事業,挺起了中國崛起的脊梁。而陳芳允在科研事業上的無私奉獻,以及對國防科技保密工作的嚴謹、忠誠,也為新一代“追星者”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懷拳拳愛國心立熠熠強國志
“望眼遍野遭欺凌,
侵我國土殺我同胞心如絞。
如有一天兩相遇,
狹路相逢絕不饒。”
——臺州亂彈劇目《追星者》戲詞片段
1916年4月,陳芳允出生于黃巖城關寺后巷的一處三進式大宅里,他5歲開蒙入私塾讀書,在黃巖中學讀完初中后一路北上求學,考取清華大學。
陳芳允在清華大學求學時,本來選擇的專業是機械系,后來受中國第一代科學家吳有訓教授的影響,改入了物理系,期間還積極參加了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運動。1937年“七七事變”后,由于戰亂,陳芳允隨學校遷往長沙,輾轉多地后進入西南聯合大學(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校聯合),繼續物理學的研究和學習。
“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。我父親曾對我們說過,人生志向應該是為國家而立。而且他動手能力強,物理實驗中用到的很多工具他都是自己動手做出來的。”陳曉南介紹,在顛沛流離中成長起來的陳芳允,目睹了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,也看到了科學科技滯后給中國帶來的血淚教訓,早早在心中埋下了一顆“科技救國”的種子。
從西南聯合大學畢業后,陳芳允曾到國民黨航空委員會的成都無線電廠工作。在此期間他發現廠領導要求導航設備對準的方向不是日本,而是延安,陳芳允意識到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性,產生了離開無線電廠的念頭。1945年,陳芳允考入到英國考瑟無線電廠研究室工作,并參與了英國第一套海洋雷達的研制。
“我父親是從抗日戰爭時期走過來的人,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,他不愿為國民黨發動內戰而工作。”陳曉南說,1949年國民黨力促陳芳允去臺灣,在李敬永(臨海籍地下黨)的幫助下,陳芳允請人以割傷腳趾的方式住院留在了上海。
抗日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前,中國的工業基礎極其薄弱,科技發展與西方國家比相差甚遠,始終以落后為恥的陳芳允,一生在科研領域奮起直追。在陳芳允的家中,一直保存著一本科學顧問聘書,聘書上的頒發日期“7月7日”,曾重重撥動了這位科學家的愛國之心。為了牢記歷史、激勵自己,陳芳允在聘書首頁曾記錄下“對日抗戰開始日,切記要壓倒日本人”的字樣。
“抗日戰爭時期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和思考,逐漸樹立了只有跟著共產黨走,才能救中國的信心和決心。”陳芳允曾在回憶錄中說。
不過問不言說擔負國之重任
“衛星好似風箏飛上天,
全憑地面測控跟蹤一線牽;
建好臺站接收裝置全鋪開,
護航東方紅一號直上九重天!”
——臺州亂彈劇目《追星者》戲詞片段
新中國建立后不久,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全面封鎖和打壓,并多次對我國進行核威脅,為了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,黨和政府把發展“兩彈一星”作為國防事業的重中之重。“兩彈一星”是國家絕密工程,它代表著中國國防高科技的崛起,代表著新中國自力更生、艱苦奮斗的民族智慧,無數科技工作者為它隱姓埋名、以身許國,直到近年,其中的感人故事才逐步披露,回顧過往,歷久彌新。
1953年,陳芳允接受黨的任務,開展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,并參加了國家12年長期科學規劃制定工作,工作“涉密”已成常態。
“我母親(沈淑敏)也是一名科研人員,她在生物物理學領域中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。”陳曉南介紹,在陳芳允帶領團隊進行核爆測試用的儀器研制時,也正值國家生物物理所的創建初期,沈淑敏作為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學方面的科研人員,參與和組織了關于核輻射對動物的急性和慢性損傷的試驗研究。夫妻二人雖然性格截然不同,但對待工作同樣嚴謹、忠誠,“不好奇、不過問、不言說”已成夫妻之間、父子之間相處的默契。
“他們在家從來不討論工作,因為我父親不愛說話又常常出差,家里幾乎全靠我母親一人打理。”陳曉南說,“記得小時候,我和我父親共用一間書房,父親的書桌是我母親不去整理的唯一區域。”在陳芳允的家中,不用沈淑敏特別強調,陳曉南和哥哥陳曉東都知道父母工作的特殊性,不去翻看父母的東西。而受家庭“不談工作”氛圍的感染,即使后來陳曉南也緊跟父親的步伐,從事衛星通信系統的研發工作,父子之間依然只聊生活、不談工作。
1965年,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研制工作正式啟動,陳芳允擔任衛星測量控制的總體技術負責人,承擔了地面測量控制設備的研制、臺站和中心的建設、軌道計算等方面的艱巨任務。中國到底哪里適合建立測控站?這些答案需要陳芳允帶著技術團隊走遍中國,翻山越嶺到人煙稀少的地區實地考察。每次離家前,陳芳允會好好吃一頓妻子做的飯,至于“要去哪兒、做什么”,又是與家人也不能言說的秘密。
“我父親經常離家大半年,家里人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,后來當我也進入國防衛星通信系統工作后,才知道他當時去的那些地方條件有多艱苦。”陳曉南說,當時,在中國廣袤大地上,綠皮火車是人們出行至外省的重要交通工具,而火車上人多眼雜,陳芳允從不放心把文件交給別人管理,“聽跟著他出行的隊員說,我父親在火車上不管去哪,文件包從不離身。我工作后,也養成了時刻警醒的習慣,一旦發現有問題的人或事,少說話多留心,不給任何可疑的人機會打探消息。”
名利淡泊如水清廉自守成墻
“度娘頭,細佬頭,
提著橘燈望星星。
要問最亮是哪一星?
頭上這顆‘芳允星’!”
——臺州亂彈劇目《追星者》戲詞片段
陳芳允的一生中,榮譽無數。1983年,他首次提出“雙星定位”概念和設想,并于1989年演示成功。他的“雙星定位通信系統”設想,比美國科學家喬漢森發表的同一設想早了15年;1985年陳芳允因參與完成微波統一測控系統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;1988年因航天測量船上電磁兼容問題的解決獲國防科技進步一等獎;1999年因在“兩彈一星”工程建設中的突出貢獻獲“兩彈一星”功勛獎章……
“四十京兆一技人,愛研求實不愛名,一稱專家已過譽,慚愧國人趕超心。”面對接踵而至的榮譽和贊揚,這句小詩卻是陳芳允最真實的內心獨白。
作為國家功勛科學家,陳芳允有足夠的能力讓自己和子女過上錦衣玉食的優越生活,可現實中,他和家人的生活堪稱清貧,頭發長了自己理,衣服破了自行縫補,哪怕因公外出住賓館,也從不要求享受特殊待遇。
“他和我母親生活節儉,卻默默資助過很多人。有一次我回家探望父親,碰巧看到有個人特地從國外回來感謝我父親,我才知道他一直在資助一些學生。”陳曉南回憶,黃巖城關原本留有一座陳家宅子,后遇到拆遷,陳芳允直接通過親屬把拆遷款捐贈給了當地小學。“我父親的愛好就是科研工作,直到去世前,他還念念不忘自己提出的有關國家空間科技發展的重大項目。金錢、名利他都不在乎,這個品質對國防科研工作者來說非常重要,不會被誘惑。”
父母的言傳身教對子女是最好的教育,陳芳允夫婦不為名利所困的豁達,也對后代子孫影響頗深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,陳曉南進入國防科工委工作,期間,因參與執行國防科工委衛星通信系統建設工程、國際海事衛星通信系統等建設工程,陳曉南的技能被國外多家衛星通信公司看中,“當時國內、國外懂得數字化通信的人才并不多,國外曾有公司提出年薪20萬美元讓我去工作,但我還是拒絕了,要知道那時我每月工資只有300多元錢,為什么要留下,因為祖國更需要我。”
由于黃巖寺后巷的陳家老宅已被拆除,陳曉楠再回黃巖,還是租住在父親兒時生活的區域附近。2024年4月份,經陳芳允家屬倡議,家屬與黃巖區共同出資設立“陳芳允獎學金”,每年將對黃巖中學部分優秀和困難學生、老師給予資助,激勵師生共同開拓創新、拼搏奉獻,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。
(部分圖片由李洲洋提供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